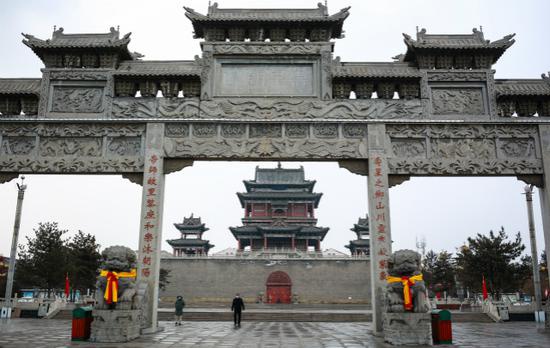武汉按下“暂停键”,我们要反思什么?

大流动中国的“暂停时刻”:一个集体反思的难得契机
【导读】2020年开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作为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此次疫情防控涉及国家治理的诸多问题。《文化纵横》杂志长期关注治理现代化问题,我们相信疫情防控定能取得胜利,也认为这一事件为我们理解国家治理在高速流动时代所面临的规律和挑战,提供了难得的反思契机。
本文是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于1月28日开展的线上集体研讨的综述,文章发问:我们到底在经历一场什么样的疫情及其带来的社会巨变?在国际格局大重组大变动的时代,类似这种突发重大风险会如何演变?文章围绕“大流动时代”特点、“大城市为王”思路、移动新媒体时代的治理难题、危急时刻的社会运转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仅代表作者观点,感谢授权,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文化纵横》杂志也欢迎广大学人赐稿,就相关新现象和新问题发表深度见解,以期共同拓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视野和智识空间。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公共危机
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思考
2020年伊始,江城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迅速吸引了全国的关注,高速流动的中国突然从武汉按下了“暂停键”,传承数千年热热闹闹访亲拜友的春节,顿时被“封城”和“隔离”等热词取代。我们到底在经历一场什么样的疫情及其带来的社会巨变?在国际格局大重组大变动的时代,这种突发重大风险是否会越来越多?我们又该汲取哪些经验?
▍一、如何治理“大流动社会”?
建国七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了“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诸多便利,在资本的牵引下,高铁、高速公路、航空、移动互联网等一系列基础设施条件的提升,中国近年以约2.5亿流动人口的规模展现着“大流动社会”的震撼与繁荣,“春运”更是其极致体现。恐怕一个月前,还没有人会认真想象过对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超大城市进行“封城”的具体情形。疫情的迅速扩大,无疑与全社会各种要素的高速流动密切相关。过去三十年,我们积累的所有治理流动社会的经验,主要是日常管理和服务为主,如治安、教育、医疗和环卫等方面。在重大突发情况下的流动社会治理,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显然还有很多可以改善提升的地方。本次疫情应对中浮现出了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如事权在央地之间的合理分工、条块之间的配合与协调、区域间的合作与排斥、城乡之间的团结与分化、基层社会的组织动员方式等等。
首先,区域分化问题再次凸显。
在此次疫情防治初期各省的行动可以发现,不同地域和省份的利益自觉要比十七年前的“非典”时期强很多。这看起来和2012年以来中央权威加强的趋势相悖,其实并行不悖。上世纪九十年代分税制改革时期,央地博弈说到底主要是在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之间的博弈,而且是在数字上锱铢必较的数目字博弈。
但这一次,是“群起而较之”,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领域的博弈,跟公共财政上的经济层面的博弈,又有明显不同。个体化时代,自保的动力较之以前更强了。这种地方民众的压力虽然未必对中央的地方官员选任机制产生什么影响,但守土有责,哪一个地方大员都不愿冒乡里之大不韪来“以身涉险”,两者一拍即合,中央则事后追认默许。就这样,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强化和中央权威的强化同时并存就可以理解了。但也需要注意到,中央迅速再次强调了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公安部也迅速强调未经批准擅自断路等行为将依法处置。
现代社会,独善其身已不可能。风险社会,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大市场、大流动社会格局下,还有何人何地能独善其身?闭门以自保的结果事实上是“七伤拳”,注定撑不了多久。上海的菜价,这两天就也是一个大型“翻车”现场。快递小哥、外来人员隔离在外,白领“在家上班”,可能吗?城市化之后要后退,一定会进退失据,甚至退一步万丈深渊,因为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经变掉了。
其次,当前城乡治理的差异性戏剧性体现。
相比于城市的“精细治理”,农村还是非常粗放的。从网上披露以及部分河南籍成员的亲身观察来看,河南有的村庄自发行动起来,有的在政府组织下行动起来,但最初应对的方式都是最直接的——堵路、封村。河南农村地区的行动能力在这次事件中彰显得淋漓尽致,但显然这还不够科学。在人口大流动时代,作为人口流出大省又比邻湖北的河南,面临大规模春节“返乡”的人潮,防疫压力空前巨大。虽然网上有“硬核”一说,但其实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信息统计能力还远远不够,而只能凸显出堵路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相比城市的精细治理,农村更多采取的是封村堵路的策略)
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城乡基层社会确实是都动员起来了,但动员的机制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治理是要精细、精准到区块、网格、人员上,城市和农村的动员机制有共同之处——城乡基层组织,但区别仍是根本性的。
这也值得思考,农村和城市的治理差异究竟是什么?
中心成员也介绍了近期亲身体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乡土社会,一种以基层组织为引导严防疫情,另一种是以人情礼俗为主导,共谋“生死之交”。
以豫北某村为例,首先,大年初一紧急通知,以村级组织为主力,封路、拉起红色布条全面戒严等等,一系列的行动让村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其实红色布条和封路的大土堆并不能彻底阻断村民进出的通道,它们更大意义上是一种信号——危险,这种危险的信号由正式组织为代表来传达。加上网络媒体的更新和朋友圈微信群里关于疫情的渲染,家家户户在大年初二就开始了足不出户的自我隔离与保护。随后,村组织只是下发了疫情防控传单,通过喇叭进行疫情防御的广播,但是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时,乡土人情就会徘徊在乡村。人情的维系来自于礼尚往来的情感和面子文化,有来无往会得罪人,不给面子也会令双方限于难堪的境地。尤其是“走亲戚”并不是单家独户的事情,是生长在亲属网中的复杂关系结构。这就出现了很多“不得不”。
两种现象的明显对比,其实证实了我们治理体制中一直强调的,社会的力量往哪里走,是需要正面而有力引导的。这种引导是行动性的,而不单单是宣传。农村中老年人一辈活在世俗的现实世界中,他们的权威信息来源主要依赖于村委。网络信息极其发达,他们没办法辨认其真伪,所以只能靠传统的正式组织权威为标杆。
▍二、“大城市为王”的利与弊?
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纵深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引擎越来越依赖于大城市,发展大都市圈成为各国的共识。中国近期也明显倾向于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的经济活力,完善改革开放的空间布局。大城市和城市群带给我们的是“效率”,这种效率既有经济发展的“正功能”,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虽然我们一直对此有理论上的讨论和警惕,但全国不分东西南北的真切感受这种“风险社会”的威力,还是罕见的。武汉为九省通衢,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还是常住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此次武汉的疫情直接带动了全国30个省区进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充分揭示了现代大都市的风险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不会因噎废食,但如何更好地提升大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已经刻不容缓。
大城市带来给我们更多地是生产效率和消费能力,凸显的是一个“力与欲”;我们阻断疫情的方法是降低流动和切断传播,入手之处是“关系”。如果仅仅从“关系”(社会组织)上反思和入手,则终究还是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或许需要的一场改变中国人生活习惯的“行为革命”,也即“生活治理”。“病从口入”依然有效,如果按照流行的说法,疫情源于大量的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所致,则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治理或许还是要从“吃”开始。我们过往比较重视“社会治理”,强调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员等,但其实中国的治国理政传统中包含着大量的“移风易俗”的“生活治理”,直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脱离开“生活治理”的社会治理是片面的,也往往是不细致的。
▍三、移动媒体时代的治理难题
此次疫情发展迅速,但全国范围内关注此事,还是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采访为转折点,此后形势发展超出所有人的预料,舆情沸腾,各类真假信息短时间里天量涌现。在人人都可以做信息源的时代,信息的真假分别顿时成了难题,我们越来越难以认清这个世界。这也是本次疫情与十七年前“非典”时期的重大不同。
面对汹涌的舆情与民情,国家如何适当引领和传播正能量?如果由舆情引发的恐慌难以遏制,其带来的潜在社会风险(如抢购生活物资等)将难以估量,也必将产生远超过疫情本身的社会代价。信息的权威发布,本身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但保障信息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一定是谨慎而需要时间的。但这种谨慎和时间周期性,在新媒体时代恰恰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广大网民在等不到权威信息的时候,往往被各类鱼龙混杂的信息所困扰。
同时,此次事件中反映出来网络在农村社会中的功能,也值得关注。之前农村社会生活中的联系,主要是串门、大街上闲聊等方式。这次事件的出现,强烈的改变了村民获得信息的方式并重塑了其观念意识,除了村干部的喇叭广播之外,多是从网络平台(抖音、西瓜等自媒体平台)获得疫情的相关信息,并迅速调整了自己的观念与行为。所以,农村社会生活的联结方式,跟网络或自媒体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
此外,微信也成了这次严控聚会空间之后,所出现的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人际之间的交往、信息流动,多是通过微信实现的。所以,从现实的面对面的交往到虚拟空间的交往,是目前农村社会交往的一个巨大变化,而在此次防疫过程中又被强力加速了。
▍四、危急时刻的社会如何运转?
如武汉市长在电视采访中所言,此前人类历史上都从来没有对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进行过“封城”。从目前的情况下,依托强大的物质保障、组织动员和技术条件,武汉市依然能够正常运转,这种史无前例的现代条件下的紧急时刻生活经验和治理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总结思考。而且城乡之间也体现出较多的差别,城市更多依赖技术,乡村更多依赖组织。
现代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转依赖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力量的协调发力,“封城”、交通管制和禁止群体性活动,更多体现的是社会交往的“暂停”,物质、信息和能源的输送依然正常,这是技术发达和物质丰裕的体现,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但“暂停键”显然不能长久为之,社会的持续正常运转,依然需要恢复市场和社会的活力。
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城市化的时代,但又是一个城乡关系极为密切的城市化阶段,“春运”及其带来的疫情传播也是一个集中体现。我们需要适应城市生活,我们需要提升文明习惯,我们需要与大自然更为和谐的相处,我们需要更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我们还需要更多勇于担当的干部和专业人员。这或许是此次疫情带给我们的一个集体反思的难得契机,当然疫情仍在继续,事态还需要持续关注,相信我们能够化危为机,克难攻关。
本文为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成员于1月28日开展的线上集体讨论的综述,讨论由中心主任熊万胜教授主持,参与讨论成员有叶敏、曹东勃、马流辉、李宽、杨君、张建雷、王阳、田雄、王欣、程秋萍、申腾、张贯磊、刘炳辉等,综述由刘炳辉执笔,熊万胜审定。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CSSCI中文核心期刊
《文化纵横》2019年12月新刊上市
✪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
(本文为中心集体研讨成果,由刘炳辉执笔,熊万胜审定)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